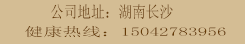(一个中篇)
1
我没法跟任何人证明艾玛小姐存在过,这是我开始讲这个故事前最担心的事。
如果我拿出那张在伦敦市中心的街头拍下的照片, 一张照片,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唬烂瞎说。但我保证,艾玛就在那张照片上。在我身后那家Nespresso的橱窗里摆放着用一千块乐高碎片拼成的伦敦桥,伦敦桥后面还有那些标志性的图案,英国国旗、红色电话亭之类的,当然也是乐高搭好的。你如果仔细地观察橱窗里的倒影,就能马上看到当时正在给我拍照的艾玛小姐。
如今我已经三年没有见过艾玛了,我离开伦敦至今也已经整整七年。
我经常在梦里回到伦敦,焦虑地走在上学的路上,担心着我下一秒就会迟到。梦里那些熟悉的气味、脚下的石板路、草坪和被刷成各自深浅蓝色的店铺,反复向我印证着我的确在哪里生活过。但是我无法证明艾玛存在过,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她,她就像是一阵微弱而混乱的脑电波,消失在我荒蛮混沌的潜意识中。
如果不是三天前我带着我的孩子大扫除,无意中在那只废旧的行李箱里找到了这张照片,我甚至不会记起我还曾有过一位这样的朋友。我的孩子从那只行李箱的夹层里摸出了那张照片,用他胖胖的小手捏住那张照片,然后指着上面的人问,“这是谁?妈妈?”
照片上只有我自己,我点点他圆圆的小脑袋,“你连自己的妈妈都不认得了吗?”
“我当然认识你了,妈妈。”我的心肝宝贝说,“我说的是后面这个人。”
我顺着他短短的手指头看去,才看到那橱窗里倒映出来的另一个人的脸。艾玛!我愣了一下,把那张照片拿起来仔细看着。那是年夏天,艾玛在橱窗倒影里里举着手机,那只手机挡住了她的眼睛,只能看到她带着的一顶滑稽的、软软的绿色毛线帽。
她咧开嘴开心地笑着,对我说,“1、2、3,cheers!”
我 次见到艾玛是在年春天,三月中旬。伦敦的三月总是多云,那些云像漂浮在天上的柔软羊群,悠闲地随风转变着形状和模样。阳光不晒,偶尔会有一阵顶着太阳落下来的雨,那些温润细腻的雨落下来的时候会在半空中变成彩虹,淡淡地挂在不远处,似乎伸出手就能触碰到。
那时候我还是艺术学院预科班的新生,从遥远的东方初来乍到,面对着满街金发碧眼的*佬和特立独行的怪人们,内心敏感,时时惶惑不安。但我知道我不能表现出来,我要维持我冷酷的表情,就像这里的每个人一样。
其实我并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。我被送到那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的父母那时候在闹离婚,我猜。他们不希望我参与到他们那僵持了三年的离婚案件中去。他们或许是担心我会目睹他们在法院里相互辱骂的丑态,又或许是担心我会用我幼稚的眼泪,可怜巴巴地哀求他们维持这个家貌合神离的原貌。
总之,他们决定送我到这个地方来,并且告诉我,“不用担心,你只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。”
我后来才意识到他们的真心话可能是,“别烦我,去那边自己玩一会儿。”
我刚去的时候住在学校的宿舍里。我记得那个地方叫做foxtons,在帕丁顿街花园西边一点,离最近的地铁站bondstreet需要走15分钟的路程。每天早上我都从宿舍出发,走路去地铁站,然后在shepherd’sbush下车,再步行去学校。正常的通勤时间要1个小时,但如果遇到地铁罢工和游行,我就要花1.5个小时才能到学校。
我通常不去别的地方,因为我不太认识路。但有一个周末,我要去伦敦城北部坎顿区找一副有名气的街头涂鸦作品。所以很早我就出门,坐公交车在greenwoods下车,然后在坎顿区大片的绿地和民宅附近走来走去,寻找我心仪已久的那副画。
就在那里,我 次遇到了艾玛。
那幅画很难找。我走了一个上午,才终于在一个居民区的后墙上找到了那副画——拉起英国国旗的男孩,涂鸦艺术家banksy的真迹。我兴奋地坐在那看着它,心满意足地把它拍下来存档。
可当我准备离开时,我才发现我找不到回车站的路了。
我像是无头的苍蝇一样在那些陌生的街道上乱转,很快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。你知道在一个治安状况不明朗的街区迷路,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异国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如果在中国我可以放心地拦的士回家,但伦敦的的士很贵,而我那微薄的生活费不允许我用几天的饭钱打一辆的士回宿舍。
正当我担忧害怕的时候,有个印巴男人开着车经过,他把车子缓缓地停在我面前,摇下车窗问,“你需要帮助吗?小姐?”我结结巴巴地向他描述我的麻烦,然后向他询问greenwoods车站的方向。
那人听完,竟然爽快地打开车门,“上来吧,我送你去车站。”我当时已经走得双腿酸痛,天气很热,我想我快要中暑了,我真的很想上那个人的车子,让这位好心人带我去车站。
可是这时候有个声音在我背后说,“如果我是你,我就不会上那个人的车。”
我转过头,一个带着绿色毛线帽的女孩子从我身后走来,她笑着对司机招招手,“谢谢你,我找到我朋友了,我可以带她去车站。”
那印巴人愣了两秒钟,他用一种被冒犯了的眼神看看我,“嘿!我不是坏人!你不相信我吗?”
艾玛搂住我的肩膀,看着他露出迷人的笑容,“非常感谢你,先生,但我们认识去greenwoods的路了。”
那司机看了她一眼,然后飞快地把车子开走了。
我看着艾玛,“谢谢,但你怎么知道我要去greenwoods?”
艾玛看着我,露出慵懒的笑容,“你是预科班的新生吧?我在开学典礼上见过你,你是哪个学院?坎伯韦尔?还是时装学院?”
“时装学院的。”我放松下来,原来她是我的校友,“那你呢?你也住foxtons吗?”
艾玛点点头,她打量着我,“你看起来不像是时装学院的。倒像是温布顿的那些土包子。”
她说话很直接,让我有些尴尬。可我不得不承认,我刚去伦敦的时候穿得的确很土气。再看看艾玛,她穿着露出肚脐和前胸的紧身内搭裙,外面套着一件柔软小巧的皮质外套,她背着的包似乎是意大利的手工包,皮质似乎比她的外套更柔软。
她随手从包里拿出烟,“你有火吗?”
我把火机拿出来给她点燃。那些白烟顺着她微微翘起的鼻子均匀地吸进去,再从她拢成圆圈的嘴唇呼出来,她看起来有一种天然的性感。她眯起眼睛看看天空,用手指把她散开的头发轻轻绾到她圆圆的后脑勺。
“走吧,我们一起回宿舍去。”艾玛又吸了口烟,“你是中国人?”她问。
我点点头。
她恍然大悟地点点头。
“shit!”她突然说了句脏话,“我误会刚才那位好心人了!”她看着我疑惑的表情解释说,“那个人是巴基斯坦人,难怪他要帮你。你们中国对巴基斯坦非常友好,所以,你知道的。”
她夹着烟的手指在半空中随便挥舞了一下。“我是意大利人,所以他对我没那么友好!难怪我刚才找他搭车他都不肯!”然后她笑了笑。“我祖母也是中国人,可他却不肯看在这四分之一血统上帮助我!这可真是不公平。”
我也笑笑,不知道该说什么,我那时甚至不知道中国和巴基斯坦很友好。
她对我伸出手,“艾玛。”她自我介绍说。
“程小一。”我握握她的手,她的手很冷,像我自己的手一样冷。
“程小一。”艾玛重复着念着那几个字。
我们走上公交车,坐在 一排。艾玛看看我,“你有没有耳机,跟我分享一下?我 在公交车上听音乐。”我点点头,要把自己的耳机从手机上拔下来,艾玛阻止我,“不用,让我听听你的音乐就好了。”
我手机里只有范宗沛的大提琴曲。
“这个也可以吗?”我问。
艾玛耸耸肩,“大提琴,中提琴,小提琴,所有音乐对我来说都一样。”她拿起一只耳机塞进耳朵里,然后把另外一只分给我,“我们可以一起听,这样就省去了聊天寒暄的尴尬。”她说着,又露出那神秘的、迷人的微笑。
我点点头,戴上耳机。
路上我很快睡着了。等我睡醒时,公交车刚好停在foxtons的公交站底下,转头看看,艾玛不见了。
2
那天之后,我很久都没有再遇到过艾玛。
我在宿舍里留意着那些陌生的面孔。艺术学院的宿舍里,怪异的打扮和年轻美丽的面孔都非常常见,但没有一张脸能让我跟那天的艾玛对上号。我甚至主动接近那些意大利裔的学生,向他们询问艾玛的消息。
安东尼来自米兰,他总在一楼会客室里抱着一些零件组装自己的装置艺术作品模型。有一次我向他问起,认不认识一个叫艾玛的女生。她是意大利人,但她说自己有中国血统,棕色的长发,细长眼睛,微微翘起的鼻子,戴一顶绿色的毛线帽。
安东尼托着下巴,饶有兴趣地看着我,“听起来是个很漂亮的姑娘。”
我点点头,继续跟安东尼形容:她身高和我差不多,大概5.7英寸,背着一只手工包,那种手工皮质的,非常好看的软皮包。安东尼停下手里的活仔细回想了一下,“意大利那种包太多了。”他耸耸肩,“但下次意大利学生聚会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去,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她。”
安东尼又把注意力放回他的作品上,他在做一个看起来像火车头一样的东西,只不过是用一堆大小不一螺母黏起来的火车头。“不过你可别误会哦!”安东尼停下来看着我,“我只是帮你找人,不是要约你。我没别的意思,你不要紧张。”
我没紧张,可安东尼看起来有点。
我赶紧点点头。
自从上次艾玛说我有点土之后,我就开始学着她的样子去买了一些新的衣服和帽子。foxtons后面的那条街上有一个集市,每周六上午都有当地人出来摆摊。他们卖自己制作的奶酪和面包,或者自己家种的郁金香和玫瑰。还有一些心灵手巧的老太太,会制作蒸馏纯露和草药肥皂,运气好的时候还有自制的鲜花香水。
这周六中午我又跑去集市上。
惊喜的是,我买到了一条看起来跟艾玛一模一样的裙子,还有一顶和艾玛头上那顶一样可笑的帽子。那帽子是一个老奶奶自己编织的,她帮我把那顶软沿帽戴在头上。“美丽的姑娘戴什么都好看!”老太太高兴地大声说,“如果你喜欢的话,10pence就可以带走了!”
我嘻嘻笑着,把那顶帽子戴在头上,想象自己像艾玛一样可爱。
从集市回来,我在房间里跟妈妈视频。她看起来心不在焉的。我问她过得怎么样?她耸耸肩,“宝贝,我最近很忙,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”
我点点头,戴上那顶帽子给她看,“妈妈,你觉得我新买的帽子好看吗?”
“这样的帽子你不是有很多了吗?”我妈妈问,“不需要买那么多一样的东西啊,宝贝。这样是很浪费钱的。”
“可是这是我 次戴这样的帽子啊…….”我摘下来看着它。
我妈妈不耐烦地看看我,“好了宝贝,我要出去了,我的朋友来接我了。你照顾好自己吧!”说着她挂了电话。
我妈妈有很多朋友。她骄傲漂亮、喜欢跳舞,喜欢跟人打交道。但我父亲不是,我父亲只喜欢工作,哪怕在家里他也总是自己待在书房的办公桌前,盯着自己电脑上的报表和图纸。只要我母亲一说话,他就忍不住把门关起来。而我母亲只要听到他的关门声,就会马上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。
我正看着屏幕发呆,门外的敲门声响起来。
打开门,艾玛正站在门外!
“hi!好久不见!”我见到她很惊喜,“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?我一直都没看到你!”
艾玛拉着我的手走进来,神秘地笑笑,“我去了一趟法国,跟几个朋友见面,还给你带了礼物。”
我看着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叠印着巴黎铁塔的彩色小方块,像是什么糖果,还有一个精致的丝质礼品袋。“猜猜这是什么?”她像魔术师一样,举着那个小袋子在我眼前晃晃。
我摇摇头,“不知道。”
艾玛笑嘻嘻地拿起那叠小方块,“这个你总知道吧?”
“糖果吗?”我笑着撕开那方块,才看到里面是避孕套。那些油粘在我手上,我厌恶地甩了甩手,然后把那只撕开的避孕套扔进垃圾箱。
我有点尴尬,艾玛却不在意地耸耸肩。“女孩子总要保护自己的!”她说着,把那叠花花绿绿的避孕套塞进我怀里,吓得我赶快把他们放在桌上。
“还有这个,”艾玛打开那小袋子,从里面拿出一颗像压片果糖一样的药片,“张开嘴。”
“不,不,我不吃……”我结结巴巴地躲开她。
艾玛把药片放进自己舌头底下,对我眨眨眼,“好孩子,你做了正确的决定。”
敲门声又响起来,艾玛快手快脚跑去开门,安东尼正站在门外。“外面在游行!快来!”他脸上涂抹着彩虹色的颜料,赤着上身招呼我们。
我愣了愣,举起手想和安东尼打招呼。
可艾玛却先大笑着,熟络地跟他拥抱在一起,艾玛热烈地搂住安东尼的脖子,给他一个法式的热吻。安东尼像是没看见我一样,搂着艾玛的腰身,转身走了出去。
我的手还停在半空中。我有点不自在。可我明白,跟艾玛站在一起,是没有男孩会看得见我的。
支持同性恋婚姻的游行在大街上热热闹闹地举行,队伍里的人都涂着彩虹色的颜料,高呼着自由和爱的口号。我站在窗口向外望去,艾玛和安东尼都赤裸着上身站在那,举着巨大的游行牌走在队伍前头。艾玛的胸部尖尖的裸露在阳光下,像一对柔软的金丝雀。
周一去上课的路上下了雨,连绵不断到细小雨滴落在地上积成浅浅的水洼,远远看去像是分散在马路上的一面面镜子。雨水细密地落在那些镜子里,像是投身于另一个世界,并跟那镜子里的世界融为一体。
我举着手机,低头看着课程表上面满满的课时心里在打鼓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,作业时常会做不完。那些密密麻麻的理论课几乎填满了整个学期的周一时段。我英文不够好,我想着,那些古典文学的莎士比亚小说研究让我害怕。如果我是艾玛就好了,她有流利的英文和法语,还会讲一点国语和广东话。要是她有时间在课业上帮帮我就好了。
我叹口气,可惜她总是在玩。
她似乎跟安东尼在一起了,她几乎一整个周末都在他的宿舍厮混。她不用写作业吗?她到底是什么专业的?她似乎从来没有担心过考试的问题…….也许她非常聪明,根本不需要为那些事担心。
唉,我可真羡慕她。
正低头胡思乱想着,我走上地铁。站在扶手栏杆的一侧,我把头靠在上面,忧心忡忡地担心着自己的作业选题。安东尼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,他低下头看着我。吓得我迅速后退一步。
“怎么了?”他看着我,然后从地铁窗子的反光里照照他自己,“我脸上有东西吗?”
“没有。没有。”我下意识地离他远一点。
呵呵,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笑笑,然后自然地把手拦到我的腰上。我赶快推开他,“你,你今天去上理论课吗?”我问。
“小心你后面。”安东尼说,“你差点儿踩到那个人的脚。”
我回头看看,背后有个穿西装的邋遢男人,正一脸油腻地盯着我的臀部。我赶紧走到地铁另一侧的扶手旁。安东尼绕到我身边,挡住那个人盯着我的视线。
“别介意,总有这样讨厌的人的。”安东尼小声安慰我,“他刚才想摸你,还好被我发现了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慌张地道谢。
安东尼眯起那双碧绿的眼睛打量着我。
“不客气,宝贝。”他说。
我不自在地缩了缩脖子,我不习惯被别人这么叫。
地铁到达Waterloo站。安东尼在这里修他装置艺术的课程。他胡乱摸摸我的头发,“下课见。”他说着,走下地铁。
下课见?
我纳闷地看看他的背影,为什么他要这么说?
(待更新谢谢
苍孙王冬妮儿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balesitana.com/btfz/446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