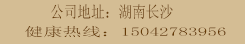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马黎整理“‘从古代西亚到早期中国’,我给自己挖了很大一个坑。”这是拱玉书先生的开场白。9月23日,“史前符号和早期文字学术报告会”在浙江平湖举行。回顾:良渚有文字吗(一)|平湖庄桥坟遗址刻文石钺发现十周年,问题比共识更重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亚述学家拱玉书先生在线上做了一次信息量极大的分享。“还好有个副标题——‘关于器物符号与早期文字的几点思考’,可以把坑填平一点。”“拱玉书先生翻译的《吉尔伽美什史诗》,刚在杭州获得了春风悦读榜金翻译家奖。”主持人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。对研讨会上未尽的内容,这几天,拱玉书又做了补充和修订,以下是他的思考。第一:器物符号的起源早于文字。这不是观点,是事实。为什么叫器物符号,而不是陶器符号呢?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有陶器,还有石器、玉器、金属器。讲文字和器物符号的关系时,必须要强调这个事实。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:楔形文字。楔形文字由苏美尔人创造,但就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判断,可能由乌鲁克人创造。公元前年代末至年代初的乌鲁克,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。楔形文字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,距今有多年。在公元前至公元前年,这多年的时间里,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在使用楔形文字,此后继续在部分地区使用,直到公元前后。在楔形文字产生之前,两河流域域和周边很多地方都出土了陶器符号。比如伊朗境内的贾法拉巴德遗址,公元前年-年,出土了35个刻划符号,位置基本都靠近器物的底部、内壁和外壁。伊朗境内的乔威遗址,在片陶片底部,发现了84个刻画符号,归纳起来有26种。有的符号出现一次,大部分符号出现三到四次,有一个符号出现了7次,就是汉语所说的“万”字的符号。这个符号在西亚史前遗址中很常见。伊拉克境内的遗址哈孙纳(Hassuna,公元前0年)出土了各种各样的“万”字刻划符号。但是,如此常用的符号,并不见于楔形文字。所以,陶器符号在西亚没有影响楔形文字的起源,就目前所知,楔形文字的起源和陶器符号没有关系。第二:器物符号自成一体,和文字并行不悖。很多史前遗址都出土了陶器符号,有的后来借用了楔形文字或者埃兰的楔形文字,借用后,器物符号依然使用,自成一体,和文字并行不悖。举一个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的例子:乌尔。这是个典型的苏美尔城市,地处伊拉克南部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乌尔王陵出土的楔形文字泥版,属于公元前2年左右。乌尔人不仅在泥版上书写,也把文字用在金银器上。比如这个金碗,刻了标准的楔形文字,这是一个王国的名字:Mes-kalam-dug3,这是这个时期非常标准的铭文体的楔形文字。有的石器上也有楔形文字,比如这个石碗(图),也是乌尔王陵出土的。但是,在其他一些器物上,人们在使用一种与文字不同的符号体系。比如这个石碗,上面连续刻了三个相同的符号,谁也不认识。但是,它和乌尔王陵出土的青铜器——矛头上面刻的符号,属于一种符号。还有一种动物形象的符号,有人说是豹,乌尔的考古报告上说是豹,我昨天在电脑上放大后一看,是四个豹并排。乌尔王陵20世纪初由英国考古学家吴雷[C.L.Woolley]主持发掘,出土了大量金银器。还有一些是和文字体系完全不同的无法解释的符号。比如这一个,良渚文化也有一个符号跟它很像。这个符号是刻在匕首上的。这说明什么?说明文字和器物符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符号体系,二者可以在不同领域,甚至同一领域同时使用,互不排斥,并行不悖。第三,器物符号的载体和文字的书写材料性质不同。文字一般书写在特殊的或者已经约定俗成的书写材料上。比如,两河流域写在泥版上,起初的文字都是书写在泥版上的,后来也有写在石板、金银器上的文字,但不是主流。主要书写材料就是泥版,或泥质材料。这是公元前年的、公元前年的,还有公元前年亚述时期的泥版和泥棱柱,都是泥质书写材料,总的来说,泥质材料是文字书写的主要材料。书写材料和文字是没有关联的,不管书写什么内容,都和泥没有关系,和六面体、八面体棱柱也没有关系。但是,器物符号就不一样了,它们和书写材料息息相关。我们先看器物上的铭文。这只石碗上,刻了铭文,这是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的石碗,距今4年。铭文里面有个动词,“我把它献给某某人”——“它”(即宾语)是什么,不需要出现。我们在说话时,及物动词后面必须有宾语,但在器物上刻写铭文时,铭文中不需要出现宾语(在这篇铭文中,宾语是“它”),什么意思呢?意思是我献的这个物,就是这个石碗,没有出现的宾语就是“这个碗”。还有一个石瓶,是乌尔纳木献给吉尔伽美什的,也没有宾语,因为宾语就是“该石瓶”。所以,刻在容器上的文字和载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二者不能分开,分开便会造成语意缺失。现在再来看陶器符号。这些单个陶器符号,出自幼发拉底河岸、叙利亚境内的Tuttul遗址,这里也发现了楔形文字,但是文字是从两河流域借来的,在公元前年左右。刻在陶器上的这些符号,实际上就是附着在陶器上的符号,这些符号和承载它们的容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不能剥离开,一旦剥离开,就失去了意义。这些符号的功能是什么?大部分认为就是陶工符号,是他的代号,或姓氏、或人名、或族名。因此,一个符号就可以代表“此器由某某人所造”。一个符号就可以代表这么多意思,只需写明制器人的名字这一个信息就够了,其他都在不言中,因为无需多言,其他信息都是约定好的。比如这三划,像是数字,我们读不懂,有可能是数字“三”,有可能代表容量单位,如“三斤”,也可能代表序列,如“第三”。但不管代表人名、容量,还是序列,只要在容器上写个“三”就足够了,“三”以外的信息都在不言中,因为都蕴含在容器本身。所以,器物符号一定要附着在器物上,两者不能分开。一旦分开,比如,如果把“三”写在其他器物,那么,此“三”就不是此“三”,而是彼“三”了,也就是说,别的器物赋予这个“三”以别的意义了。第四,陶器符号没有普遍的社会意义。先来看TepeYahya出土的一组陶器符号。这是一个伊朗境内的遗址,由哈佛大学和伊朗联合发掘。排除形相近的符号,比如麦穗的形,这个符号几乎什么地方都有,这个遗址发现了个符号,最早的属于公元前年,和良渚差不多。绝大部分为公元前年-公元前年。年,波茨教授(D.Potts),一位悉尼大学的考古学家,在《古代东方》(Paléorient7,)上发表了一篇论文。他把陶器符号分为两种,一种是手工制造的,一种是陶轮制造的,而陶器符号都出现在手工制造的陶器上,陶轮制造的陶器上没有。为什么?因为手工制作的陶器都是在家庭小作坊自己做的,再拿到公共窑里去烧(这是他的推测,窑没有发现)。所以必须刻上符号,以便在出窑时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产品。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,很有启发性。波茨教授是考古学家,观察得比较细,不知他的观察是否对良渚陶器符号的研究有借鉴意义?陶器符号有几个功能。我和葛英会老师、颜海英老师合著的《文字比较研究》中有一章“论陶器符号在文字起源中的作用”,我们把西亚地区的陶器符号,还有中国的和埃及的,都搜集了一番,对各国的研究者的观点也进行了归纳。关于陶器符号的功能,大致有如下说法:陶工符号(谁做的)、工场标记(在哪做的)、顾客标记(为谁做的)、容量标记(多大)、内容标记(里面装什么)、数字、魔力符号、族徽、死者的名字,等等。第五,器物符号没有规范,也不可能形成规范。来看一个叙利亚的遗址出土的陶器,上面有很多符号,比如麦穗。这个符号在楔形文字中是个字,即大麦。但这个符号是不是大麦,是作物还是植物?谁也说不清楚。这个符号很普遍,在很多文化中都有。这里有很多符号和良渚符号相似。这些符号是一个符号的不同写法?还是相互有别的不同符号?我认为它们是一个符号的不同写法,陶器符号的书写应该没有规则,多一划,少一划,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区分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“日”,写法不同,我认为都是一个符号,早期的文字都有很多异体,就更不用说陶器符号了,多一笔,少一笔,出点头,不出头,都没关系。再举一个例子,这是伊朗境内的一个遗址,叫Shahdad,出土了多个符号,不包括异体字,即不包括那些符号形状类似、但又不尽相同的符号。如果把不同的异体符号都算作是一个符号,都看作独立符号的话,符号的总数在个以上。乌鲁克出土的早期文字有个左右,在年出版的乌鲁克字表中(见M.W.Green/HansJ.Nissen主编的ZeichenlistederArchaischenTexteausUruk,Gebr.MannVerlag,Berlin),基本形状相同、细节有出入的符号都被视为一个符号的异体,如sag(“头”)这个符号,有19种写法,但被视为一个字,它们也的确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。这说明,早期文字也没有规范的写法,一次一个样,一人一个样,只要八九不离十即可。就西亚地区的原始楔形文字而言,在一个遗址(乌鲁克)就出土了0多个块泥版,使用的符号(除掉异体)还有多个。而且这个时期的文献,不但有经济文献,还有辞书文献,包括百工表、树木表、容器表,等等。这么发达的文字,西方学者尚且称之为“原始楔文”(Proto-cuneiformwriting),那么,在他们眼里,我们的良渚符号就很难成为文字了。仅就文字或符号的发达程度而言,我们的良渚符号的确与原始楔文不在一个层次上,但良渚文明的发达程度是显而易见,它确是那个时代的一座文明高峰。六,陶器符号不必然演化为文字。在文字产生之前,在两河流域以及周边地区,西到地中海沿岸,东到伊朗,甚至阿富汗、巴勒斯坦这一带,出土了很多陶器符号。但任何一个遗址的陶器符号都没有发展成文字。有的遗址的居民借用了楔形文字来书写,同时继续使用陶器符号;有的遗址的居民几百年、甚至上千年使用陶器符号,最终也没有发明文字。文字是发展的,会根据社会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,如果一种符号体系不向前发展,甚至几百年不出现成篇的文献,那么,这种符号体系就很难称得上文字。古代南亚地区的哈拉帕文明长期使用一种印章文字,符号有几百个,但这种文字几百年没有多大发展,这样的文字就令人匪夷所思了。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SteveFarmer先生甚至认为哈拉帕的印章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,原因就是这种符号体系几百年始终没有什么发展。据目前所知,陶器符号,或者写在其他特定器物上的符号,比如印章上,都没有发展成文字。像萨马拉、埃利都,都曾有陶器符号,但没有一种陶器符号发展成了文字,楔文也没有借用这些陶器符号的例子,一例都没有。说到这里,拱玉书普及了一下楔形文字的起源。比如陶筹论。楔形文字是从哪里来的?陶筹论认为不是从陶器符号来的,而是从陶筹发展来的。陶筹有个发展过程,从简单发展到复杂,然后到陶筹封球,再发展到陶筹印纹。也就是把陶筹封进封球之前,在封球上压上印。拱先生举了一例:一个陶筹封球上有六个印迹,三个圆形的印迹,三个长形印迹,打开封球后,发现里面有三个圆形陶筹,三个长形陶筹。显然,陶筹与陶筹印迹不但形状相符,数量也相符。毫无疑问,封球上的印迹是把陶筹装到封球里之前印上去的。封球上的陶筹印迹与三维的陶筹有同样的意义,即表示同样的概念或代表同样的数值。既然印迹能表达信息,或代表数值,那么,封球和陶筹就可以不要了,在泥版上直接压印,或刻字(数字)就可以了,于是便产生了数字泥版。数字泥版产生后,文字泥版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这就是楔形文字的陶筹起源论。美国德州大学的D.Schmandt-Besserat教授是陶筹论的倡导者,她在《文字之前》一书中还比较了几十个陶筹与文字的形状。显然,陶筹是楔形文字在创制过程中取形的源泉之一。陶筹与楔字的形相似也成为楔文起源于陶筹论者的根据之一。第七,文字是发明的,不是长期发展的结果。徐天进和拱玉书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:文字是发明的,是由一个或一些贤者在短时期内创造的。拱玉书更坚定一些,确信楔文是发明的,不是发展的结果。陶筹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,这跟文字没关系。但是,它一旦启发了造字的思想,一大批文字一下子就诞生了,这些突然出现的文字就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创造的,它们没有演进史,但取形时,造字者参照了陶筹,而绝大多数单体文字都是根据具体的实物取形的。单体字诞生之后,造字者又根据一些原则,在已经造出的单体字的基础继续造字。这些原则,由于时间的关系,拱先生没有来得及涉及。有一篇苏美尔语文学作品讲到了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。按照苏美尔人的观点,文字是英雄造的,这位英雄,就是乌鲁克的国王,叫恩美卡。那时的苏美尔,有国有王,有神有庙,但是国家发展需要远程贸易,楔形文字就是在进行远程贸易的过程中发明的了。在苏美尔人那里,文字不是人民大众造的,不是由任何东西演变而来的,而是国王恩美卡发明的。现在已知的发达文字,比如中国的甲骨文,埃及的象形文字,西亚的楔形文字,这三种原生的古文字都没有经过长期发展演变之后成为文字的证据。我们在苦苦寻找发展的过程,但我们可能误入了歧途,文字是发明的,不是发展的结果。任何试图找到文字长期演化发展的努力,可能会付诸东流。最后一点,中国最早的文字用软笔书写,不晚于丁公陶文的年代。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丁公陶文是文字(少数人持不同意见)。从是文字这个前提出发,丁公陶文给我们如下启示:1、丁公陶文所代表的文字体系(指的不是丁公陶文)是用软笔书写的,写出来的字比较圆润(如冯时先生当年[]说的,有“曲笔、圆笔和弧笔”),这种圆润的字已经成为这种文字(未知文字)的定式,所以,用尖器(什么质料的尖器不详)在陶片上(丁公陶文)书写时,书写出来的字也呈圆润态,也就是说,书写者用尖器在陶片上书写时,是按传统的手法、约定俗成的字形来书写的,这种用软笔书写在有机材料(具体不详)上的字,其产生时间至少不晚于丁公陶文的年代。2、从字形和运笔特点(风格)看,丁公陶文与甲骨文不属于同一个书写体系。3、如果不属于同一个书写体系,记录的语言也不一定是汉译(有人认为是彝文,记载是古彝语)。丁公陶文最后,拱玉书讲到良渚陶器符号,认为良渚的器物符号错综复杂,反映出早期符号体系一些不同的特点,而这些特点的背后可能蕴藏着鲜为人知的文化面貌:1、简单的刻符可能是陶工的代号(名、姓或族)、也可能代表器物种类(盛麦或稻米)、也可能是数字(表示器物的容量);2、贯耳壶上的四个符号或五个符号似与汉字有一定关联,董楚平释为“方钺会矢”,似有道理,但似乎也可以作其他解释;苏州澄湖良渚文化遗址的水井发现的泥质黑陶贯耳壶,上面有五个连续排列的符号3、黑皮陶罐上的12个符号大概率是一幅文字画;余杭南湖遗址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圈足罐,上面有12个符号4、石钺上的六个字有可能是字母文字,重复率高是字母文字的显著特征。但是,目前已知的字母都不早于公元前年,而且中国这片土地上也不曾存在字母文字的传统,所以,这个推测过于大胆。或许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,这六个符号代表的文字(如果是文字的话)是音意文字,埃及的文字象形,而这六个良渚符号所代表的文字体系的符号更抽象?这只是印象驱使的不着边际的推测。但不论如何,良渚符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给人一种印象:良渚可能是个多文化的交汇点。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石钺A面上的刻符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,未经许可,禁止转载、复制、摘编、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,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。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balesitana.com/btfz/12312.html
![]() 当前位置: 巴勒斯坦 > 巴勒斯坦发展 > 良渚有文字吗二拱玉书文字是发明的,不
当前位置: 巴勒斯坦 > 巴勒斯坦发展 > 良渚有文字吗二拱玉书文字是发明的,不
![]() 当前位置: 巴勒斯坦 > 巴勒斯坦发展 > 良渚有文字吗二拱玉书文字是发明的,不
当前位置: 巴勒斯坦 > 巴勒斯坦发展 > 良渚有文字吗二拱玉书文字是发明的,不